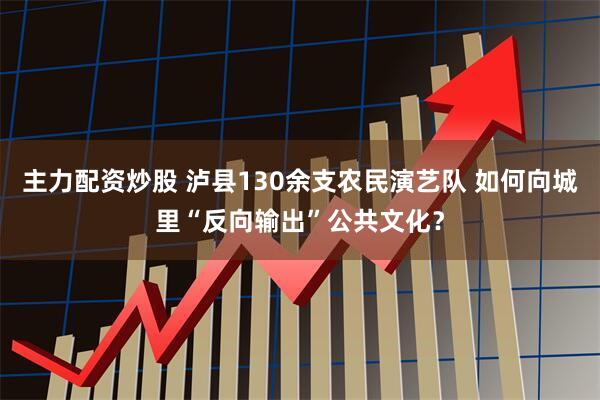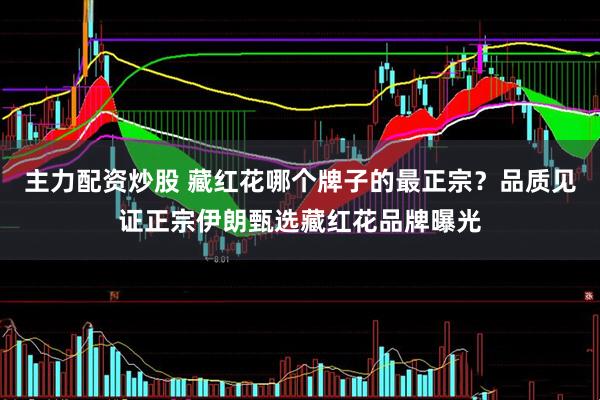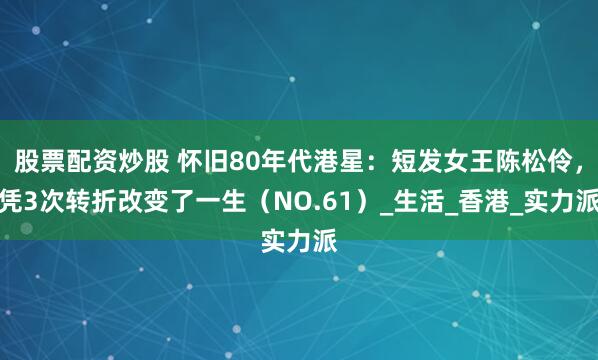文/甘海斌
近日余读《历代散文选》中司马迁之文——《甘罗十二为上卿》,掩卷沉思,心潮难平。一个十二岁的少年,竟能在群雄逐鹿的战国舞台上,以一言而易数城,以片语而移国运,终获上卿之位,此非天方夜谭,而是太史公笔下的真实传奇。
甘罗,何许人也?他是战国末期秦国政治家,生于公元前约256年,是秦国左丞相甘茂之孙。他自幼以聪慧过人著称,年仅十二岁便成为秦国相国吕不韦的门客,以其睿智脱颖而出。
展开剩余82%据《史记·樗里子甘茂列传》记载,公元前244年,甘罗主动请缨出使赵国。他利用纵横之术,成功说服赵王,主动割让五座城池给秦国,以成“联秦之势”。随后,赵国发兵攻打燕国,夺取了燕国上谷地区的三十余座城。按照与甘罗的约定,赵将其中的十一座城献给了秦国。甘罗此计,使秦国兵不血刃,最终获得了赵国割让的五城和攻燕后献上的十一城,共计十六座城池,扩展了疆域。因其功绩卓著,甘罗被秦王政(即后来的秦始皇)封为上卿(相当于丞相之位),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外交家之一。甘罗的传奇生涯短暂而辉煌,其事迹彰显了战国时代谋士的智慧与外交策略的重要性,成为古代少年英才的象征。
余为甘氏,通读太史公之文,觉得格外亲切。笔尖流淌的不只是冰冷史迹,更是血脉相连的家族记忆。那位十二岁的少年,不仅是史家笔下的奇才,更是我甘氏一族的精神图腾。他的故事穿越千年时光,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,映照出个体与时代相互成就的深刻哲理。
甘罗之功,堪称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典范。当秦国欲联燕攻赵遭遇阻碍,丞相吕不韦尚且无策之际,这位少年却以过人胆识请命出使。他先以白起、范雎旧事说张唐,言简意赅直指利害:“应侯欲攻赵,武安君难之,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邺。今文信侯自请卿相燕而不肯行,臣不知卿所死处矣。”此言一出,宿将悚然从命。
其后使赵,甘罗更展纵横家本色,直面赵襄王,剖析秦燕联盟之威胁,提出“赵攻燕而秦不救”之妙策,终使赵国献上五城。这番外交斡旋,既免兵戈之祸,又得实地之利,其战略眼光与谈判艺术,令后世子孙引以为豪。
然细究甘罗之成功,非仅凭个人才智,更得益于战国特殊之时势。春秋以降,礼崩乐坏,至战国时期,各国争霸已达白热化。旧有的宗法制度渐趋瓦解,世卿世禄不再是晋身的唯一途径。列国为求生存与发展,竞相招揽人才,而不问出身、不论年龄。
秦尤甚之,自商鞅变法以来,便形成“有功者显荣,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”的功利主义氛围。李斯《谏逐客书》中“太山不让土壤,故能成其大;河海不择细流,故能就其深”之语,正是这种人才观的生动写照。甘罗的脱颖而出,恰是这股时代洪流所孕育的奇迹——若非身处这样一个唯才是举、注重实效的时代,纵有通天之才,亦难有施展之地。
作为甘氏后人,我们既为先祖的智慧而自豪,也理性审视其历史意义。甘罗之奇,重在辩才与临机应变,属外交策士之才,与通过系统改革奠定国基的政治家,在历史影响上存在维度之差。其成功极大依赖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与战国末年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,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性。
然其故事至今仍熠熠生辉,正因它提醒我们:人才的涌现需要开放包容、唯才是举的社会机制。昔燕昭王筑黄金台,郭隗建言“帝者与师处,王者与友处,霸者与臣处,亡国与役处”,唯有尊贤重才,方能汇聚四方英杰。
余从甘茂列传中,不仅见一位少年之机智果敢,更窥见一个时代之气象精神。纵观历史,甘罗如一颗流星,在战国夜空中划出短暂却耀眼的光芒。其成功是个人天赋与时代机遇碰撞出的火花,更是我甘氏一族永续传承的精神财富。
当今之世,欲使人才辈出,亦需营造开放多元、任人唯贤的环境,让各类英才不论资历、不囿常规,皆能脱颖而出。先祖甘罗之智,可赞可叹;而其所以能成甘罗之时代,尤当深思。太史公将这位少年的事迹载入史册,或许正是要后世铭记:真正伟大的时代,从不会因年少而轻视任何一颗智慧的种子——这既是历史的镜鉴,也是我甘氏子孙永志不忘的家训。
乙巳之秋於京华馨心斋
发布于:湖北省鑫耀证劵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